吕思勉三癖:好弈、嗜烟、爱猫
发布时间:2022-11-01 09:11:01作者:准提咒结缘网
吕思勉三癖:好弈、嗜烟、爱猫
吕思勉是一位把廿四史读过三遍的史学大师。在他传世不多的照片里,总给人不苟言笑的印象,似乎只知道苦读史书。实际上,除史学外,吕思勉兴趣广泛,也多有著述。他谙熟中医,著有《医籍知津》;在文学上,他不但擅长诗词,有《蒿庐诗稿》与《梦秋词》;早年还创作过中篇小说《中国女侦探》,还著有理论专著《小说丛话》。
对崇拜的大师,学术粉丝很难做到钱钟书说的那样,假如你吃了个鸡蛋,觉得不错,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即便无缘面谒,粉丝们也奢望知晓些大师的细节。那么,让我也来八卦一下他在学术外的那些癖好吧。
好弈
吕思勉说自己“不善棋而颇好弈”,七八岁时,见了棋谱就喜好。日后,他几乎收齐了传世的象棋残谱,“久置书簏中”。十二三岁时,他旁观父亲与姑父对弈,“乃略知死活”,据此推断,这里说的是围棋。不过,他认为他俩“棋皆极劣,不能教予”;母亲严管其读书,也不准他下棋。
1903年,吕思勉赴南京参加晚清末次乡试,有暇便到夫子庙茶肆观看围棋高手束云峰与汪叙诗对弈。1905年起,吕思勉在故乡常州教小学,结识了苏州学者刘脊生等棋友,脊生还与他通函论弈。1911年,他客居南通,曾与围棋名手陈饯宾对弈,对方约定让他三子。
民国以后,吕思勉在上海结识了常州姜鸣皋、吴伯乔与其他棋坛人士,包括在刻印古棋谱上颇有贡献的邓元鏸。姜鸣皋参与过公车上书,为官安徽时“所至宏扬棋道”;他曾注范西屏的《四子谱》,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;还有弈友诗20余首,可惜散佚。《围棋纪事诗》说姜鸣皋:“姜被怡怡气宇昂,公车爱国热心肠。注传诗失良堪惜,余教犹能衍异乡。”也难怪吕思勉评骘常州籍弈人,“以姜君鸣皋为最高,吴君伯乔、屠君雄卿次之”。
吕思勉棋艺如何?据其自述,1918年客寓苏州时“技术亦稍进”,已与屠雄卿旗鼓相当。1920年起,他任教沈阳高师,自称“沈无弈人,三年中只与北京魏君华萱相遇,曾弈,弈数局耳。华萱亦北京名手,技稍逊于予也”。吕思勉决非自吹自擂之辈,据此推断,他的棋艺应该相当不错。
三年以后,吕思勉自沈阳南归,基本不下棋,但偶尔还会技痒。此后他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,也关注那些棋艺优长生。据他说,“学生中好围棋者二人,曰顾颂德、常熟郑之骧,技视予皆少忧”。足见他与学生有时也会对弈,否则何以知棋艺知优劣!
吕思勉不但自己嗜棋,还以学者身份研究棋谱与棋理。1918年,他校阅了清代王再越的《梅花谱》,在识语中比较了象棋与围棋的异同,对两者棋谱行世的多寡,决胜棋法的精粗,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他还认为,博戏容易“长行险徼幸之心,益凭陵叫嚣之气”,不如棋艺“专恃智力,以决胜负,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,所谓‘其争也君子’”。八年后,他为这册校本新写了篇识语,交付文明书店出版。
1925年,吕思勉与棋王谢侠逊在《上海时报》的《象棋质疑栏》上以通信方式探讨棋艺。他不仅请谢侠逊到校讲解棋局,指导学生;还建议棋王搜辑汇刻传世象棋谱,“为前此精于艺事者昭悬万古,亦足为国家艺术增光”。1928年,他还为谢侠逊的《象棋秘诀》作序,强调棋理错综变化,“固与一切事物同”:“必始于至简,由是推之繁。惟至简者之所知不讹,则稍繁者之所推可信”。吕思勉从棋理悟出的是历史的逻辑,这与他民国初年那首论弈棋诗是一脉相通的:
静思世事与棋同,负局支持苦到终。
一著偶差千劫定,输赢毕竟太匆匆。
抗战时期,吕思勉避敌居乡,有时也“观谱下棋消遣”,如有会棋的学生来访,他也会邀下几局,甚至赠以自己校印的《梅花谱》。一位学生问他,能否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棋盘运子的所有变化,编成棋谱,稳操胜券。吕思勉回答:“说不定将来会有一种计算的机械,得以解决这样的难题。要是当真如此,以机械代替技艺,弈棋的兴味将大大减低。弈棋的兴味,在乎斗智,并非斤斤计较胜负。胜与负,同样可以长进智慧。”这与他“其争也君子”说是一以贯之的。
吕思勉下棋的兴味至老不衰。1954年,他回故居养病,还常找友人弈棋。其11月22日日记云:“至大庙弄人民银行交电费,拥挤,至顺兴,拟小坐复往,与浦寿观围棋两局,遂逾银行办事时矣。自三月二十九日在和平与项君弈,归而病,自此未弈也。”大半年因病没过棋瘾,为过一把瘾,竟误了缴电费,活脱脱一个嗜棋邻叟的可亲形象。1957年,大师已到生命的尽头,还写了长达七页的《弈棋之经历》,回忆了交往的弈友,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棋史文献。
嗜烟
披卷研究之暇与伏案著述之余,史学大师吕思勉也喜欢抽上两口烟,作为精神调节,这是他不多的嗜好之一。
研究专家张耕华说,“吕思勉喜欢吸水烟,烟叶偏好福建产的皮丝烟”。据其所著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谱主四岁那年,其母日记云:“接闽信,桔叶膏、汀烟”,这汀烟应即福建皮丝烟。她是吸水烟的,其1908年四月日记说,“初八四句半钟至上海,夜半轮船转湾,民船转柁稍迟,桌间面盆、水烟筒、茶杯皆坠于地”。吕思勉抽水烟或受母亲的影响,历史也相当悠久。早在20岁日记里,他就记及,“午后购笺、信纸,并购□信、皮丝、白糖、信封等件”。次年,其《甲辰日记》也记道:“午后到九华取扇未得,并购茶心、皮丝,在第一楼啜茗。”这年吕思勉与夫人虞菱完婚,婚后常在苏沪等地执教。吸水烟须纸煤(也叫纸尺)引燃,这种纸煤以易燃的黄裱纸斜卷而成,松紧适度,中呈空心状,一头打成纸结,卷纸煤颇费时间。据张耕华说,吕思勉“每次回家省亲,虞菱总是为他搓好许多‘纸尺’。吕思勉身体单弱,外出或去上海时,随身所带的行李很少,但虞菱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藤篮的纸尺却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1914年春夏之际,吕思勉客居海上,与友人赵元成(赵元任的堂兄)、丁捷臣等共结诗社,半月集会一次,命题赋诗,切磋诗艺。一次,丁捷臣出题《水烟》,吕思勉赋诗两首。其一云:
谁切黄金作细丝,由来此物最相思。
清芬绝胜含鸡舌,酩酊何劳举鹤卮。
并世几人留醒眼,吾徒颇藉疗朝饥。
当年欲笑穷边叟,醉倒田间不自持。
首句描述了金黄色烟叶切丝加工的过程,一个“谁”字,表明他购买的应是加工好的烟丝,次句以最堪相思譬喻嗜烟之情,也别具趣味。第三四句渲染了吸烟的快感,那清芬之味绝对胜过口含鸡舌香,而飘然酩酊之感简直让人不必再举鹤型杯而畅饮不已。五六两句戏谑抽烟的功用,有了烟瘾后,举世没几人能保持清醒的眼光;而我等只仰赖它疗治早辰的腹饥而已。想当初嘲笑过荒僻边远的老汉,讥嗤他抽烟后醉卧田间而不能自持的憨态,实在大可不必。
其二云:
深闺长日镇相怜,笑杀如兰总自煎。
星火更资杯水力,斜风疑袅瑑炉烟。
微波喜与樱唇近,锦字重劳玉腕镌。
试共从头追往事,遐方荒冢倍缠绵。
这首诗摹写妇女抽水烟的情状,研究者认为,“是吕思勉与夫人虞菱拉家常时一起唱吟而成的”。闺房幽深长日无事,不妨抽烟慰籍那百无聊赖。“如兰”也许暗指虞菱(字繸兰),笑看像她那样总是自煎自吸。点点火星全仗杯水过滤,斜风袅袅疑似雕纹香炉在冒烟。樱唇总对着烟管吹拂微波,闲来无事还劳柔腕书写锦字回文。结尾两句写夫妇抽烟聊天,尝试着一起从头追说往事,说到那遥远的荒冢让人倍感悱恻缠绵。
结社评诗时,赵元成评“二律刻划入细,似可存”,但“微波与杯水意复,能否酌改”。吕思勉对游戏之作并不满意,自评“近纤,拟删”,打算殳落之。
据学生回忆,吕思勉待人接物“态度平易近人,不管与同辈或青年人交谈,都是诚恳相待。
吕思勉晚年气喘得厉害,应与其长期嗜烟有关。他自置“医事备检”的文档,收藏着常州名医唐玉虬的函札,告知他“置旱烟管上吸之以治喘者,为风茄花,此物稍有毒性,亦不可多吸”。另存弟子汤志钧的便笺,也说及“洋金花可置于烟斗中服之,治气喘,但久服有弊。风茄花舍亲曾查询《本草》未见,不知是否别名?”看来,一生嗜烟终究害苦了这位史学大师。
爱猫
弈棋之外,吕思勉的另一爱好就是养猫。据他回忆,“年九岁始好猫”,当时家里养两只猫。老白猫性凶猛,他“畜兔二、画眉一,皆为所杀,然不恶之也”,仍视为“猫友”。另一只董猫“甚美”,因获之堂姑董家而得名,母亲特意送他饲养。这年,他随父赴江浦县学教谕任,“携之往江北,恐其失去,恒闭房门,不许其入院落,久乃释之”。在那里吕思勉新养三只猫,与董猫分别名为“志道”、“据德”、“依仁”与“游艺”,连为猫命名都寄寓着志趣。五年后,匆匆南归,董猫恰外出,未能携归,吕思勉“后常痛惜之”。
新婚不久,其父允诺将名唤“大龙”的牡猫送给归宁的二姑。吕思勉将大龙私下寄放友人处,“二姑既行,乃又抱之归,家人但以为猫适出而已,不知予与予妻所匿也”。他与新妇的爱猫之心跃然纸上。吕思勉说,“予妻最爱猫,家中之井用后必以物盖之,防猫之失足而坠也”。有人嗤笑她过虑,史学大师竟动用考据功夫,引证《辍耕录》坐实古已有其事,“则以物掩井,亦谨慎之一道也”。吕思勉爱猫几近痴迷。一日,他过常州东门外,一只金黄色的猫卧在养老堂东庑下,“见而美之”,堂中人原就讨厌这猫,见他留恋忘返状,就说:你喜欢,就带回去。吕思勉大喜:“汝肯送致我家,当畀汝钱二百。”那人果然高兴地送了来。
1936年,吕思勉写了好几篇猫的随笔。《猫友纪》引用孟子“舜之居深山之中,与木石居,与鹿豕游”,主张“友岂必其人也哉”,逐一追记相处过的猫友。在《太平畜》里,他将《春秋》张“三世”之说移之于家畜观:
犬者,乱世之畜也,养之以猎物,并以残人。牛马者,升平之畜也,人役其力以自利。猫者,太平畜也,人爱其柔仁,与之为友,而无所利也。
吕思勉还为猫编撰专史,题曰《猫乘》,汇辑了所能搜到的古今中外猫的掌故,例如《猫寿》、《猫食》、《猫相》、《猫赛》等等。在一个猫哺幼鼠“子之如子”的故事后,他就“嗜杀非猫本性”有感而发道:
嗟乎,人之异于禽兽者,岂皆善于禽兽者哉!禽兽不知其恶而蹈之,人知其恶而犹独为之,其不可恕甚于禽兽,不待再讨矣,然人岂生而恶者哉?吁乎!(《猫哺鼠》)
这通猫论袒裎出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。据出版家范泉说,上海“孤岛”时期,吕思勉“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,如《武士的悲哀》、《眼前的奇迹》等,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”,所用笔名有一个就叫“野猫”,也可见他对猫的钟爱。有一段时间,他常在信笺一角盖上他自刻的猫图案印章,“章仅盈寸,造型简朴,苍劲如汉印”。
学生回忆,每与常州来的乡亲谈完正事,吕思勉总会问一句:“到我家,见过阿黄吗?”他还曾津津乐道地“向同好者介绍上海城隍庙马戏团见过的一只头大、脸圆、毛长、尾粗的波斯猫”,而“头大、脸圆、毛长、尾粗”正是其相猫经的独得之见。1948年,他与学生逛邑庙,在宠物铺看到一只白色卷毛波斯猫,但索价“稻米十石”,只好望“猫”兴叹,“细细观赏了好一会才离去”。
猫成为吕家最受呵护的小生灵,吃饭时爬上饭桌,把吕思勉筷上的菜打下来吃,他也不生气,仅笑笑而已。据其爱女回忆,常州故居原有一架葡萄,每到初夏绿荫沉沉,却招来了壁虎。有一次,一只小猫突然死了,怀疑误食了小壁虎,“为保护别的小猫,就把葡萄掘掉了”。还有一次,名叫“黑大”的猫在堆放杂物而无人居住的楼上产仔,一天,它下楼找到吕夫人虞菱哀鸣不已,逐之不去,随之登楼,只见“小猫罥于网篮之绳不得脱”,几将毙命,“乃为解之”。吕思勉据此写了《猫救子》的随笔。由于吕家的善待,邻猫遁入习居为常,邻人也往往窃取猫之美者“来献以邀赏”。
1955年,故居来信说,名叫“小黄”的猫“四日不归”,或“为畜鸽者所杀”。吕思勉积忧成梦,数日后“夜梦在高台之边,见下有猫黄色,予警呼小黄归矣,欲垂绳救之,未果后醒”。两年后,吕思勉去世,其夫人在其遗体边放一支钢笔、一块表与一张猫的相片,与他诀别:
笔一支,表一只,是你生前常用之物;猫,是你生前最喜爱的动物。现在,你就把这些东西带去了吧!
明人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吕思勉好弈怡性,嗜烟有瘾,爱猫成癖,其深情真气也当作如此观。
(本文原标题为《大师三癖》)
吕思勉是一位把廿四史读过三遍的史学大师。在他传世不多的照片里,总给人不苟言笑的印象,似乎只知道苦读史书。实际上,除史学外,吕思勉兴趣广泛,也多有著述。他谙熟中医,著有《医籍知津》;在文学上,他不但擅长诗词,有《蒿庐诗稿》与《梦秋词》;早年还创作过中篇小说《中国女侦探》,还著有理论专著《小说丛话》。
对崇拜的大师,学术粉丝很难做到钱钟书说的那样,假如你吃了个鸡蛋,觉得不错,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即便无缘面谒,粉丝们也奢望知晓些大师的细节。那么,让我也来八卦一下他在学术外的那些癖好吧。
好弈
吕思勉说自己“不善棋而颇好弈”,七八岁时,见了棋谱就喜好。日后,他几乎收齐了传世的象棋残谱,“久置书簏中”。十二三岁时,他旁观父亲与姑父对弈,“乃略知死活”,据此推断,这里说的是围棋。不过,他认为他俩“棋皆极劣,不能教予”;母亲严管其读书,也不准他下棋。
1903年,吕思勉赴南京参加晚清末次乡试,有暇便到夫子庙茶肆观看围棋高手束云峰与汪叙诗对弈。1905年起,吕思勉在故乡常州教小学,结识了苏州学者刘脊生等棋友,脊生还与他通函论弈。1911年,他客居南通,曾与围棋名手陈饯宾对弈,对方约定让他三子。
民国以后,吕思勉在上海结识了常州姜鸣皋、吴伯乔与其他棋坛人士,包括在刻印古棋谱上颇有贡献的邓元鏸。姜鸣皋参与过公车上书,为官安徽时“所至宏扬棋道”;他曾注范西屏的《四子谱》,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;还有弈友诗20余首,可惜散佚。《围棋纪事诗》说姜鸣皋:“姜被怡怡气宇昂,公车爱国热心肠。注传诗失良堪惜,余教犹能衍异乡。”也难怪吕思勉评骘常州籍弈人,“以姜君鸣皋为最高,吴君伯乔、屠君雄卿次之”。
吕思勉棋艺如何?据其自述,1918年客寓苏州时“技术亦稍进”,已与屠雄卿旗鼓相当。1920年起,他任教沈阳高师,自称“沈无弈人,三年中只与北京魏君华萱相遇,曾弈,弈数局耳。华萱亦北京名手,技稍逊于予也”。吕思勉决非自吹自擂之辈,据此推断,他的棋艺应该相当不错。
三年以后,吕思勉自沈阳南归,基本不下棋,但偶尔还会技痒。此后他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,也关注那些棋艺优长生。据他说,“学生中好围棋者二人,曰顾颂德、常熟郑之骧,技视予皆少忧”。足见他与学生有时也会对弈,否则何以知棋艺知优劣!
吕思勉不但自己嗜棋,还以学者身份研究棋谱与棋理。1918年,他校阅了清代王再越的《梅花谱》,在识语中比较了象棋与围棋的异同,对两者棋谱行世的多寡,决胜棋法的精粗,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他还认为,博戏容易“长行险徼幸之心,益凭陵叫嚣之气”,不如棋艺“专恃智力,以决胜负,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,所谓‘其争也君子’”。八年后,他为这册校本新写了篇识语,交付文明书店出版。
1925年,吕思勉与棋王谢侠逊在《上海时报》的《象棋质疑栏》上以通信方式探讨棋艺。他不仅请谢侠逊到校讲解棋局,指导学生;还建议棋王搜辑汇刻传世象棋谱,“为前此精于艺事者昭悬万古,亦足为国家艺术增光”。1928年,他还为谢侠逊的《象棋秘诀》作序,强调棋理错综变化,“固与一切事物同”:“必始于至简,由是推之繁。惟至简者之所知不讹,则稍繁者之所推可信”。吕思勉从棋理悟出的是历史的逻辑,这与他民国初年那首论弈棋诗是一脉相通的:
静思世事与棋同,负局支持苦到终。
一著偶差千劫定,输赢毕竟太匆匆。
抗战时期,吕思勉避敌居乡,有时也“观谱下棋消遣”,如有会棋的学生来访,他也会邀下几局,甚至赠以自己校印的《梅花谱》。一位学生问他,能否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棋盘运子的所有变化,编成棋谱,稳操胜券。吕思勉回答:“说不定将来会有一种计算的机械,得以解决这样的难题。要是当真如此,以机械代替技艺,弈棋的兴味将大大减低。弈棋的兴味,在乎斗智,并非斤斤计较胜负。胜与负,同样可以长进智慧。”这与他“其争也君子”说是一以贯之的。
吕思勉下棋的兴味至老不衰。1954年,他回故居养病,还常找友人弈棋。其11月22日日记云:“至大庙弄人民银行交电费,拥挤,至顺兴,拟小坐复往,与浦寿观围棋两局,遂逾银行办事时矣。自三月二十九日在和平与项君弈,归而病,自此未弈也。”大半年因病没过棋瘾,为过一把瘾,竟误了缴电费,活脱脱一个嗜棋邻叟的可亲形象。1957年,大师已到生命的尽头,还写了长达七页的《弈棋之经历》,回忆了交往的弈友,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棋史文献。
嗜烟
披卷研究之暇与伏案著述之余,史学大师吕思勉也喜欢抽上两口烟,作为精神调节,这是他不多的嗜好之一。
研究专家张耕华说,“吕思勉喜欢吸水烟,烟叶偏好福建产的皮丝烟”。据其所著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谱主四岁那年,其母日记云:“接闽信,桔叶膏、汀烟”,这汀烟应即福建皮丝烟。她是吸水烟的,其1908年四月日记说,“初八四句半钟至上海,夜半轮船转湾,民船转柁稍迟,桌间面盆、水烟筒、茶杯皆坠于地”。吕思勉抽水烟或受母亲的影响,历史也相当悠久。早在20岁日记里,他就记及,“午后购笺、信纸,并购□信、皮丝、白糖、信封等件”。次年,其《甲辰日记》也记道:“午后到九华取扇未得,并购茶心、皮丝,在第一楼啜茗。”这年吕思勉与夫人虞菱完婚,婚后常在苏沪等地执教。吸水烟须纸煤(也叫纸尺)引燃,这种纸煤以易燃的黄裱纸斜卷而成,松紧适度,中呈空心状,一头打成纸结,卷纸煤颇费时间。据张耕华说,吕思勉“每次回家省亲,虞菱总是为他搓好许多‘纸尺’。吕思勉身体单弱,外出或去上海时,随身所带的行李很少,但虞菱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藤篮的纸尺却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1914年春夏之际,吕思勉客居海上,与友人赵元成(赵元任的堂兄)、丁捷臣等共结诗社,半月集会一次,命题赋诗,切磋诗艺。一次,丁捷臣出题《水烟》,吕思勉赋诗两首。其一云:
谁切黄金作细丝,由来此物最相思。
清芬绝胜含鸡舌,酩酊何劳举鹤卮。
并世几人留醒眼,吾徒颇藉疗朝饥。
当年欲笑穷边叟,醉倒田间不自持。
首句描述了金黄色烟叶切丝加工的过程,一个“谁”字,表明他购买的应是加工好的烟丝,次句以最堪相思譬喻嗜烟之情,也别具趣味。第三四句渲染了吸烟的快感,那清芬之味绝对胜过口含鸡舌香,而飘然酩酊之感简直让人不必再举鹤型杯而畅饮不已。五六两句戏谑抽烟的功用,有了烟瘾后,举世没几人能保持清醒的眼光;而我等只仰赖它疗治早辰的腹饥而已。想当初嘲笑过荒僻边远的老汉,讥嗤他抽烟后醉卧田间而不能自持的憨态,实在大可不必。
其二云:
深闺长日镇相怜,笑杀如兰总自煎。
星火更资杯水力,斜风疑袅瑑炉烟。
微波喜与樱唇近,锦字重劳玉腕镌。
试共从头追往事,遐方荒冢倍缠绵。
这首诗摹写妇女抽水烟的情状,研究者认为,“是吕思勉与夫人虞菱拉家常时一起唱吟而成的”。闺房幽深长日无事,不妨抽烟慰籍那百无聊赖。“如兰”也许暗指虞菱(字繸兰),笑看像她那样总是自煎自吸。点点火星全仗杯水过滤,斜风袅袅疑似雕纹香炉在冒烟。樱唇总对着烟管吹拂微波,闲来无事还劳柔腕书写锦字回文。结尾两句写夫妇抽烟聊天,尝试着一起从头追说往事,说到那遥远的荒冢让人倍感悱恻缠绵。
结社评诗时,赵元成评“二律刻划入细,似可存”,但“微波与杯水意复,能否酌改”。吕思勉对游戏之作并不满意,自评“近纤,拟删”,打算殳落之。
据学生回忆,吕思勉待人接物“态度平易近人,不管与同辈或青年人交谈,都是诚恳相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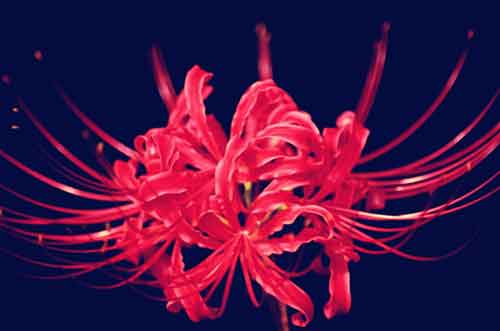
吕思勉晚年气喘得厉害,应与其长期嗜烟有关。他自置“医事备检”的文档,收藏着常州名医唐玉虬的函札,告知他“置旱烟管上吸之以治喘者,为风茄花,此物稍有毒性,亦不可多吸”。另存弟子汤志钧的便笺,也说及“洋金花可置于烟斗中服之,治气喘,但久服有弊。风茄花舍亲曾查询《本草》未见,不知是否别名?”看来,一生嗜烟终究害苦了这位史学大师。
爱猫
弈棋之外,吕思勉的另一爱好就是养猫。据他回忆,“年九岁始好猫”,当时家里养两只猫。老白猫性凶猛,他“畜兔二、画眉一,皆为所杀,然不恶之也”,仍视为“猫友”。另一只董猫“甚美”,因获之堂姑董家而得名,母亲特意送他饲养。这年,他随父赴江浦县学教谕任,“携之往江北,恐其失去,恒闭房门,不许其入院落,久乃释之”。在那里吕思勉新养三只猫,与董猫分别名为“志道”、“据德”、“依仁”与“游艺”,连为猫命名都寄寓着志趣。五年后,匆匆南归,董猫恰外出,未能携归,吕思勉“后常痛惜之”。
新婚不久,其父允诺将名唤“大龙”的牡猫送给归宁的二姑。吕思勉将大龙私下寄放友人处,“二姑既行,乃又抱之归,家人但以为猫适出而已,不知予与予妻所匿也”。他与新妇的爱猫之心跃然纸上。吕思勉说,“予妻最爱猫,家中之井用后必以物盖之,防猫之失足而坠也”。有人嗤笑她过虑,史学大师竟动用考据功夫,引证《辍耕录》坐实古已有其事,“则以物掩井,亦谨慎之一道也”。吕思勉爱猫几近痴迷。一日,他过常州东门外,一只金黄色的猫卧在养老堂东庑下,“见而美之”,堂中人原就讨厌这猫,见他留恋忘返状,就说:你喜欢,就带回去。吕思勉大喜:“汝肯送致我家,当畀汝钱二百。”那人果然高兴地送了来。
1936年,吕思勉写了好几篇猫的随笔。《猫友纪》引用孟子“舜之居深山之中,与木石居,与鹿豕游”,主张“友岂必其人也哉”,逐一追记相处过的猫友。在《太平畜》里,他将《春秋》张“三世”之说移之于家畜观:
犬者,乱世之畜也,养之以猎物,并以残人。牛马者,升平之畜也,人役其力以自利。猫者,太平畜也,人爱其柔仁,与之为友,而无所利也。
吕思勉还为猫编撰专史,题曰《猫乘》,汇辑了所能搜到的古今中外猫的掌故,例如《猫寿》、《猫食》、《猫相》、《猫赛》等等。在一个猫哺幼鼠“子之如子”的故事后,他就“嗜杀非猫本性”有感而发道:
嗟乎,人之异于禽兽者,岂皆善于禽兽者哉!禽兽不知其恶而蹈之,人知其恶而犹独为之,其不可恕甚于禽兽,不待再讨矣,然人岂生而恶者哉?吁乎!(《猫哺鼠》)
这通猫论袒裎出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。据出版家范泉说,上海“孤岛”时期,吕思勉“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,如《武士的悲哀》、《眼前的奇迹》等,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”,所用笔名有一个就叫“野猫”,也可见他对猫的钟爱。有一段时间,他常在信笺一角盖上他自刻的猫图案印章,“章仅盈寸,造型简朴,苍劲如汉印”。
学生回忆,每与常州来的乡亲谈完正事,吕思勉总会问一句:“到我家,见过阿黄吗?”他还曾津津乐道地“向同好者介绍上海城隍庙马戏团见过的一只头大、脸圆、毛长、尾粗的波斯猫”,而“头大、脸圆、毛长、尾粗”正是其相猫经的独得之见。1948年,他与学生逛邑庙,在宠物铺看到一只白色卷毛波斯猫,但索价“稻米十石”,只好望“猫”兴叹,“细细观赏了好一会才离去”。
猫成为吕家最受呵护的小生灵,吃饭时爬上饭桌,把吕思勉筷上的菜打下来吃,他也不生气,仅笑笑而已。据其爱女回忆,常州故居原有一架葡萄,每到初夏绿荫沉沉,却招来了壁虎。有一次,一只小猫突然死了,怀疑误食了小壁虎,“为保护别的小猫,就把葡萄掘掉了”。还有一次,名叫“黑大”的猫在堆放杂物而无人居住的楼上产仔,一天,它下楼找到吕夫人虞菱哀鸣不已,逐之不去,随之登楼,只见“小猫罥于网篮之绳不得脱”,几将毙命,“乃为解之”。吕思勉据此写了《猫救子》的随笔。由于吕家的善待,邻猫遁入习居为常,邻人也往往窃取猫之美者“来献以邀赏”。
1955年,故居来信说,名叫“小黄”的猫“四日不归”,或“为畜鸽者所杀”。吕思勉积忧成梦,数日后“夜梦在高台之边,见下有猫黄色,予警呼小黄归矣,欲垂绳救之,未果后醒”。两年后,吕思勉去世,其夫人在其遗体边放一支钢笔、一块表与一张猫的相片,与他诀别:
笔一支,表一只,是你生前常用之物;猫,是你生前最喜爱的动物。现在,你就把这些东西带去了吧!
明人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吕思勉好弈怡性,嗜烟有瘾,爱猫成癖,其深情真气也当作如此观。
(本文原标题为《大师三癖》)





